 |
 |
 |
出版:志光出版社
書名:法粹--通用六法
售價:NT$360元
具體分類法規體系,歸納出七大篇,分別為:中央法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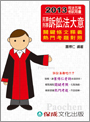
|
出版:保成出版社
書名: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大意-2013司法五等考試用書
售價:NT$520元
系統分類考點全現 按章排序釐清架構
關鍵條文概念釋義

|
|
|
 |
|
|
【實務見解掃描】被告地位的形成?
刑事訴訟法 - 被告地位的形成?關係人的定位?偵查機關先以證人身分加以傳喚取得證言,後將其轉為被告加以起訴,並將原先取得之證言作為其自白,試問該「自白」有無證據能力?
壹、被告地位的形成?
被告地位的形成。
學說上有主觀說、客觀說,但皆難以使用。如果純用偵查機關主觀認知,會很容易出現恣意擅斷的情形,侵害到被告的主體地位,因為有可能實際上執行的已經是對被告的偵查動作,但偵查機關還不覺得自己已經將這人鎖定為被告了;如果用客觀判斷,換個角度想,會是侵害偵查機關行使偵查權限時的判斷空間,譬如偵查機關真的就還不清楚案情到底為何,在路上看到真正的犯人某甲,但警察不知道他就是犯人,隨口問問知不知悉犯罪情節,如果說這樣就要指責警方沒有踐行告知義務,也未免強人所難。因此,兩難之間,通說主張要以主、客觀混合判斷,除偵查機關的主觀認知程度之外,還要參酌客觀上程序進行的種類、程度,以該行為事實上呈現出來的訴訟法上意義為準。
貳、關係人的定位
1.實務上很常使用「關係人」這樣的名詞去通知該人到場接受訪談、問話,可是「關係人」在刑事訴訟法上到底是屬於什麼樣的身分,其實很有爭議。如果說,關係人=被告,那在問關係人的時候,就要踐行告知義務這些規定,可以保持緘默、可以選任辯護人;如果關係人=證人,那在訊問他的時侯,就要踐行證人的拒絕證言權等相關告知義務。由此可知,確定關係人到底是什麼身分是有其重要性的。
2.第一個實務見解:關係人就是關係人,不是被告,也不是證人。
※法務部法檢字第 0090047562 號函
(一)按刑事程序之被告與犯罪嫌疑人均屬涉嫌犯罪之人,依現行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原則上法院審判中及檢察官偵查中,稱之為被告,司法警察機關調查中,則稱之為犯罪嫌疑人,俾從其稱謂之不同,而區分其所處之刑事程序階段,此觀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八條檢察官所從事偵查之對象為被告,第二百三十條、第二百三十一條之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所調查之對象為犯罪嫌疑人;第七十一條偵查中、審判中傳喚之對象為被告,,第七十一條之一司法警察(官)通知之對象為犯罪嫌疑人,又同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犯罪嫌疑人受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者亦同等規定意旨自明。
(二)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另有可能涉嫌之人,但未經訊問調查前難以確信其犯嫌,除依法傳喚作證,得以「證人」身分傳喚訊問之外,同法第六十三條前段規定:「審判長、受命推事、受託推事或檢察官指定期日行訴訟程序者,應傳喚或通知訴訟關係人使其到場。」因此,依上開規定,於偵查中對於尚非顯然已具備被告、證人等特定身分之人,應可以「關係人」之身分「通知」其到場。至傳票為具有間接強制性質之訴訟文書,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僅限於被告(第七十一條)、證人(第一百七十五條)、鑑定人(第一百九十七條準用人證之規定及第二百七十四條)、通譯(第二百十一條準用人證之規定及第二百七十四條)及審判日期之被害人或其家屬(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項)適用之,「關係人」則不宜使用。本部七十年十一月五日法(七十)檢字第一三五四五號函略以:避免於傳票上使用「關係人」字樣,即為同一旨趣。
(三)惟上開受訊問人,無論是「證人」或「關係人」,在訊問中如一旦發現其涉嫌犯罪之證據,且身分將轉變成為被告時,此際應即時告知其身分之轉變事由,並依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之規定告知其權利事項,如其表示欲選任辯護人,並應准許之。如此對於該受訊問人之訴訟權利保障應可兼顧,且就其成為被告後之訊問內容,亦具有被告供述之適格。如該關係人之陳述日後可能作為其他案件之證言者,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編總則第十二章證據章之規定,於訊問前告知其證人權利義務及踐行具結之規定,使該陳述內容具有證言之適格。
3.第二個實務見解:關係人就是證人。
※93年台上字第2884號判決
(五)按刑事被告乃程序主體者之一,有本於程序主體之地位而參與審判之權利,並藉由辯護人協助,以強化其防禦能力,落實訴訟當事人實質上之對等。又被告之陳述亦屬證據方法之一種,為保障其陳述之自由,現行法承認被告有保持緘默之權。故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左列事項:一、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二、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三、得選任辯護人。四、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此為訊問被告前,應先踐行之法定義務,屬刑事訴訟之正當程序,於偵查程序同有適用。至於偵查中所謂之關係人,並未於刑事訴訟法定明其屬性,惟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規定:「法院就被告本人之案件調查共同被告時,該共同被告準用有關人證之規定」,可知除被告本人在其本人之案件中具有被告之身分外,其餘相關之人,實為人證之身分,如以其之陳述為證據方法,因其並非程序主體,亦非追訴或審判之客體,除有得拒絕證言之情形外,負有真實陳述之義務,且不生訴訟上防禦及辯護權等問題。倘檢察官於偵查中,蓄意規避踐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所定之告知義務,對於犯罪嫌疑人以關係人或證人之身分予以傳喚,令其陳述後,又採其陳述為不利之證據,列為被告,提起公訴,無異剝奪被告緘默權及防禦權之行使,尤難謂非以詐欺之方法而取得自白。此項違法取得之供述資料,自不具證據能力,應予以排除。如非蓄意規避上開告知義務,或訊問時始發現關係人或證人涉有犯罪嫌疑,卻未適時為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之告知,即逕列為被告,提起公訴,其因此所取得之自白,有無證據能力,仍應權衡個案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侵害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對於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害或實害等情形,兼顧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審酌判斷之。
4.學說通說見解:證人。只要是被告以外之第三人,定性上就是證人。
參、偵查機關先以證人身分加以傳喚取得證言,後將其轉為被告加以起訴,並將原先取得之證言作為其自白,試問該「自白」有無證據能力?
被告有緘默權,沒有真實陳述義務;證人有不自證己罪權利,但是有真實陳述義務。如果偵查機關為規避被告擁有之權利,而以證人地位加以傳訊所得之陳述,這樣的偵訊是否合法?
1.早期實務見解:
蓄意:等同於詐欺取得自白,§98、§156無證據能力。
非蓄意:§158-4權衡。
※92年台上字第4003號判決
惟查:(一)刑事被告乃程序主體者之一,有本於程序主體之地位而參與審判之權利,並藉由辯護人協助,以強化其防禦能力,落實訴訟當事人實質上之對等。又被告之陳述亦屬證據方法之一種,為保障其陳述之自由,現行法承認被告有保持緘默之權。故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左列事項:一、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二、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三、得選任辯護人。四、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此為訊問被告前,應先踐行之法定義務,屬刑事訴訟之正當程序,於偵查程序同有適用。至證人,僅以其陳述為證據方法,並非程序主體,亦非追訴或審判之客體,除有得拒絕證言之情形外,負有真實陳述之義務,且不生訴訟上防禦及辯護權等問題。倘檢察官於偵查中,蓄意規避踐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所定之告知義務,對於犯罪嫌疑人以證人之身分予以傳喚,命具結陳述後,採其證言為不利之證據,列為被告,提起公訴,無異剝奪被告緘默權及防禦權之行使,尤難謂非以詐欺之方法而取得自白。此項違法取得之供述資料,自不具證據能力,應予以排除。如非蓄意規避上開告知義務,或訊問時始發現證人涉有犯罪嫌疑,卻未適時為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之告知,即逕列為被告,提起公訴,其因此所取得之自白,有無證據能力,仍應權衡個案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侵害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對於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害或實害等情形,兼顧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審酌判斷之。
2.近期實務、通說見解:
以上這則判決是在較早期(92年)作成的,現在又稍微有些變化。這個變化的原因是因為實務跟學說都發現到了證人不自證己罪的告知義務(§186Ⅱ)的問題。蓄意的部分,一樣都是沒有證據能力並無問題,有問題的是在非蓄意部分。簡言之,用證人身分傳訊時,一定不會做§95告知義務,但是有沒有做§186Ⅱ不自證己罪的告知呢?這就不一定了。
(1)檢察官未告知,違反§186Ⅱ:
實務見解:
※96台上字第1043號判決
(四)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其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條第一項關係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處罰者,得拒絕證言,同法第一百八十一條定有明文。證人此項拒絕證言權(選擇權),與被告之緘默權,同屬其不自證己罪之特權。九十二年二月六日修正公布前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三款規定:「證人有第一百八十一條情形而不拒絕證言者,不得令其具結。」修正後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二項,增訂法院或檢察官於「證人有第一百八十一條之情形者,應告以得拒絕證言」之義務。凡此,均在免除證人因陳述而自入於罪,或因陳述不實而受偽證之處罰,或不陳述而受罰鍰處罰,而陷於抉擇之三難困境。此項拒絕證言告知之規定,雖為保護證人而設,非當事人所能主張,惟如法院或檢察官未踐行此項告知義務,而告以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七條第一項「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並依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一百八十九條規定「命朗讀結文後為具結」,無異強令證人必須據實陳述,剝奪其拒絕證言權,所踐行之訴訟程序自有瑕疵。其因此所取得之證人供述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分別情形以觀:(1)、其於被告本人之案件,應認屬因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所定均衡原則為審酌、判斷其有無證據能力,而非謂純屬證據證明力之問題;(2)、至若該證人因此成為「被告」追訴之對象,則其先前居於證人身分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及法定正當程序理論,應認對該證人(被告)不得作為證據。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販賣改造手槍予牟振宇,係採取上訴人於九十三年九月十七日另案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不利己之陳述為證據。然查,上訴人於該期日係檢察官偵辦牟振宇持有系爭改造手槍一案之證人,檢察官使上訴人以證人身分具結作證,並未踐行上開告知義務,有訊問筆錄可稽(見同上偵查卷第一五三、一五八頁)。此項違反告知義務所取得之供述證據,既有違不自證己罪及法定正當程序,則於證人自己為被告之案件,自難認具有證據能力。
學說見解:
學說通說都是認為對於該證人(日後變被告)應無證據能力,只是推論有些差異。一說認為是國家機關用「具結義務與偽證處罰規定」這種不正方法取得,要依§156Ⅰ否定證據能力;一說是法未明文,就回歸§158-4權衡後認為應無證據能力。
(2)司法警察(官)未告知:
這邊有問題,問題在於司法警察在詢問證人時,到底有無不自證己罪權利的告知義務。看條文,§196-1Ⅱ並沒有準用到§186Ⅱ,所以光看條文的結論是司法警察在詢問證人時是沒有拒絕證言的告知義務的。因此實務見解也就跟你講沒有告知義務(文義解釋嘛):
※97年台上字第5299號判決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又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使用通知書通知證人到場詢問,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亦定有明文,但依同條第二項規定,並無準用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條至第一百八十九條關於證人具結之規定,是司法警察(官)並無命證人具結之權限,自無依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二項告知證人得以拒絕證言之義務。
可是學說通說就不怎麼認為了,因為本於不自證己罪權利的規範保護目的,不應該在訊問主體不同下就有所不同,§196-1Ⅱ有準用§181,代表證人仍受不自證己罪原則保護,證人有權利,可是你不跟證人講他有權利是啥意思?因此這是個立法漏洞,應該要類推§186Ⅱ,司法警察(官)詢問證人時,仍應有不自證己罪權利的告知義務才是。那既然沒告知,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就應該沒證據能力。
(3)有告知:
蓄意用證人身分傳訊的話,就算有告知還是屬於不正方法,§98、§156排除證據能力,此部分沒問題。
非蓄意的部分:重點在陳述有無任意性。有任意性,有證據能力。
※98年台上字第5952號判決
惟查:(一)、具有共犯關係之共同被告在同一訴訟程序中,兼具被告及互為證人之身分。倘檢察官係分別以被告、證人身分而為訊問,並各別踐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二項之告知義務,使該共同被告瞭解其係基於何種身分應訊,得以適當行使各該當權利,不致因身分混淆而剝奪其權利之行使,則檢察官此種任意偵查作為之訊問方式,尚難謂為於法有違。至若同時以被告兼證人之身分兩者不分而為訊問,則不無將導致共同被告角色混淆,無所適從或難以抉擇之困境。其因此所取得之供述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分別情形以觀:(1)、被告消極不陳述之緘默權與證人負有應據實陳述之義務,本互不相容。共同被告在同一訴訟程序中同時併存以證人身分之陳述,囿於法律知識之不足,實難期待能明白分辨究竟何時為被告身分、何時係居於證人地位,而得以適時行使其各當該之權利;並因檢察官係同時告以應據實陳述之義務及偽證罪之處罰等規定,亦不無致共同被告因誤認其已具結,而違背自己之意思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因此妨害被告訴訟上陳述自由權之保障。準此,共同被告就自己部分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得否作為證據,端視其陳述自由權有無因此項程序上之瑕疵受到妨害為斷。如已受妨害,應認與自白之不具任意性同其評價。(2)、被告之緘默權與免於自陷入罪之拒絕證言權,同屬不自證己罪之範疇,兩者得以兼容併存,並無齟齬。行使與否,一概賦予被告、證人之選擇,並非他人所得主張。就共同被告所為不利於其他共同被告之陳述而言,固亦有類如前述之角色混淆情形,然因該共同被告就此係居於證人之地位而陳述其所親自聞見其他共同被告犯罪經過之第三人,無關乎自己犯罪之陳述,如檢察官已踐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告知證人有拒絕證言之權利,則該共同被告基於證人身分所為不利於其他共同被告之陳述,係其行使選擇權之結果,雖檢察官同時又贅餘告知被告之緘默權,然此兩種權利本具有同質性,互不排斥,是以此項程序上之瑕疵,並不會因此造成對該共同被告陳述自由選擇權之行使有所妨害,其此部分之陳述,自得作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之證據。並因於判決本旨及結果不生影響,而不得執為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資料來源:保成法政網站-實務見解掃描
|
|
|
